有一类价值投资者采用采用一种强硬的方法,坚持强调低估值的指标。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烟蒂股”以低估指标为特征,这无疑使得一些价值投资者把这个特征提升为他们投资过程中的核心考虑因素。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价值指数(Value Index)的编制仅仅通过价值排序(基于最低的平均市盈率、市销率、市净率)与成长排序(基于最高的三年销售和盈利增长和12个月的价格变化)之比,在标普500指数中找出比率最高的1/3公司。换句话说,价值指数里的股票主要是那些以“低估值指标”为特征,而“成长”最不明显的。但是“低估值指标”远不等同于“低估”。投资者很容易被低估值指标所吸引,但是低市盈率的股票,只有在当前的盈利和最近的盈利增长可以延续到未来,才可能是便宜。仅仅追求低市盈率指标可能让你走入所谓的“价值陷阱”:数据上看起来便宜,但其实并不便宜,因为它们经营存在问题或者因为导致这些估值的销售和盈利在未来不可复制。
另一方面,成长投资阵营出现于1960年代早期经济繁荣时,60年代我在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证券研究部门开始我的投资生涯。投资者对于高增长的兴趣导致了所谓的漂亮50股票,这些股票成为许多货币中心银行(包括我的雇主)的投资重点,货币中心银行是当时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漂亮50包含了50家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成长最快的企业:这些公司被认为如此优秀,以至于“不会遇到任何困境”,它们的股票“什么价格都不算高”。在狂热之中,随着漂亮50的公司盈利增长,估值上升到很高的水平,连续多年股价表现非常好,直到1972-1974年间股价从高处直线下降。由于股价崩盘,连续多年的持有期回报为负数。凄惨的股价让我失去了权益研究总监的工作(但让我被分配到创立基金投资高收益和可转换债券——我的转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从崩盘前的高点计算,漂亮50中真正能够持续增长的公司(大约是其中的一半)在接下去的25年里产生了优异的回报,意味着对于极其少数的公司,非常高的估值在长期中可以被基本面所消化。
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这两个方面,在过去50年把投资世界分成两半。不仅形成了投资思想的不同学派,同时是用在不同产品、经理和组织的标签。基于这种区分,有一个计分板持续地评估两种阵营的表现。今天可以看到在过去10多年,价值投资的表现落后于成长投资,2020年尤其如此,因此有些人宣称价值投资已死,而另外一些人断言价值投资的复苏即将开始。与安德鲁的交谈促使我在过去一年深入地反思,我更加相信价值和成长两者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视为相互排斥的。我们很快讨论这点。
投资视角
霍华德·马克斯:关于价值投资中的成长股投资Vantage Point
我和安德鲁的讨论中,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待投资的角度很不一样。
我在1960年代开始形成我的投资哲学。当时,投资的思想还在发展中,当时主导的是本·格雷厄姆所拥护的哲学。巴菲特仍然在寻找他的最后一口“烟蒂”,还没有造出“护城河”这个词,指维持优质生意的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我的哲学的形成背景是我在1969年开始工作,经历过漂亮50的泡沫和崩溃。
1978年,我从权益投资转向可转换债券和高收益债券这类固定收益投资,进一步塑造了我的哲学。很重要的一点是,格雷厄姆和他没有那么知名的合著者大卫·多德把债券管理定义为“负面的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总的来说,债券投资者的回报是有封顶的,包括承诺的利息以及到期日按照面值偿还本金;这就是为什么债券被称为“固定收益”。结果就是如果债券还本付息的话,所有6%回报率的债券的回报率持有到期的回报就是6%。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债券没有还本付息,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简单来说,想要提高债券投资的表现,不是通过你买入哪个还本付息的债券(因为所有收益率6%的债券如果付款的话收益率是相同的),而是通过你排除掉了哪些债券(也就是说,你是否可以避免买入不会付款的债券)。很明显,这跟权益很不相同,对于权益,向上的空间理论上是无限的,这要求投资者聪明地平衡向下的风险和向上的潜力。
想成为一个好的权益投资者,我想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无疑,权益投资不适合灾难预言者。另一方面,“乐观的债券投资者”的说法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债券基本上缺乏潜力让长期回报超过承诺收益率,债券投资主要是要求怀疑和关注负面。我在固定收益上表现好的原因之一是这适合我保守的天性。因为技术公司发行的债券相对较少,我对技术没什么关注,我一直没有很大的兴趣,总觉得我无法理解。无疑我不是技术的“早期用户”,我也没有在新兴技术发展的婴儿期就看到趋势。
最后,我的父母生于1900年代早期,他们成年的时候正好是美国大萧条,我的思考过程被他们所经历的缺乏和恐惧所影响。他们经历的痛苦让他们知道金钱的重要性,以及世事多变。他们担心未来和失去的可能性。我成长中伴随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和“为雨天做准备”这类警句。这样的生活经验与父母比我的父母晚10年或者20年后出生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过匮乏,也可能没有听过这些警句。这些影响和经历使得我采纳价值投资的方法,形成“购买便宜货”的性格,这在我所选择的领域很适合,现在这个市场被称为“信贷市场”。
安德鲁的心态很不相同。显然,他早期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很不同,没有被大萧条之类的东西留下印记。他很早就接触投资,年轻的时候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投资。尽管他很欣赏我的哲学的某些要素,例如理解投资者心理的重要性、专注于基本面、以及逆向思维,他形成了自己的道路,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他的第一个阶段是“巴菲特迷”,阅读了这位投资之神的一切著作,对他的哲学亦步亦趋。但是慢慢地,他发展出了自己的观点,转向主要投资于技术和其它成长型企业。他主要的时间用来关于他和两个合伙人创立的风投公司TQ Ventures,但同时他也管理我们家庭的“向上导向的投资”且取得优异的结果。(我相应地管理我们更加保守的投资)。
这种观点的对比,特别是在2020年,产生了非凡的讨论和学习的机会。从这里开始,我所写的大部分内容是安德鲁让我在人生的第75年里开始重视的。
价值和成长:错误的二分法
The False Dichotomy of Value and Growth
在某些时刻,价值和成长的阵营几乎和敌对的政治派别的狂热的坚持一样。你宣誓对某一派别效忠,你未来的投资行动就此定型。你相信你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轻蔑另外一个派别。我想,很可能因为情感经历、知识倾向以及对于科技创新的理解,投资者很自然地被某一个派别所吸引。两者存在很明显的差异:
价值股,以今天的现金流和资产价值为锚,理论上“更安全”,有更多的保护,尽管比较不可能赚到那些预期在遥远的未来销售和盈利快速增长的公司的巨大回报。
成长投资经常需要对那些时不时会面临严重的挫折的未经证实的商业模式具有信心,要求投资者有坚定的信念,因此可以坚持住。
上涨时,成长股的股价经常包括一定程度的乐观,在修正的时候将会蒸发掉,即使是最坚定的投资者也备受考验。因为成长股的大部分价值取决于遥远未来的现金流,在现金流折现分析中需要大量折现,因此利率的变化对于它们的估值的影响相比估值主要来源于近期现金流的公司大很多。
尽管有这些差异,我不相信那些著名的价值投资者有意造成价值股和成长股的泾渭分明:前者专注于今天、低价和可预测性;后者专注于快速发展的公司,即使估值很高。这样的区分也不是核心的、自然的或者有什么用途,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复杂的世界。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投资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视价值投资为坚持基本面的商业分析,不去研究市场价格。正如巴菲特所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现金流折现适用于评估任何生意……我们大脑里没有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的区别。”只是恰好他们投资的某个时期在烟蒂股领域有大量的机会存在,特别是考虑到他们一开始投资的资金规模都相对较小,因此他们专注在烟蒂股。但当世界演变的时候,投资的机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俗谚有云:“对于一个拿着铁锤的人来说,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钉子。”关于价值和成长的区别的广泛讨论让有些人相信他们只拥有锤子,而事实上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工具箱。现在我们身处的复杂世界要求一系列的工具才能取得成功。
声明:本文係轉自網絡,版權不屬於本網站且本文观点不代表計然財經立场。如有不妥之處,煩請聯繫删除。網址:https://jirancaijing.com/huaerjie/valuevsgrowth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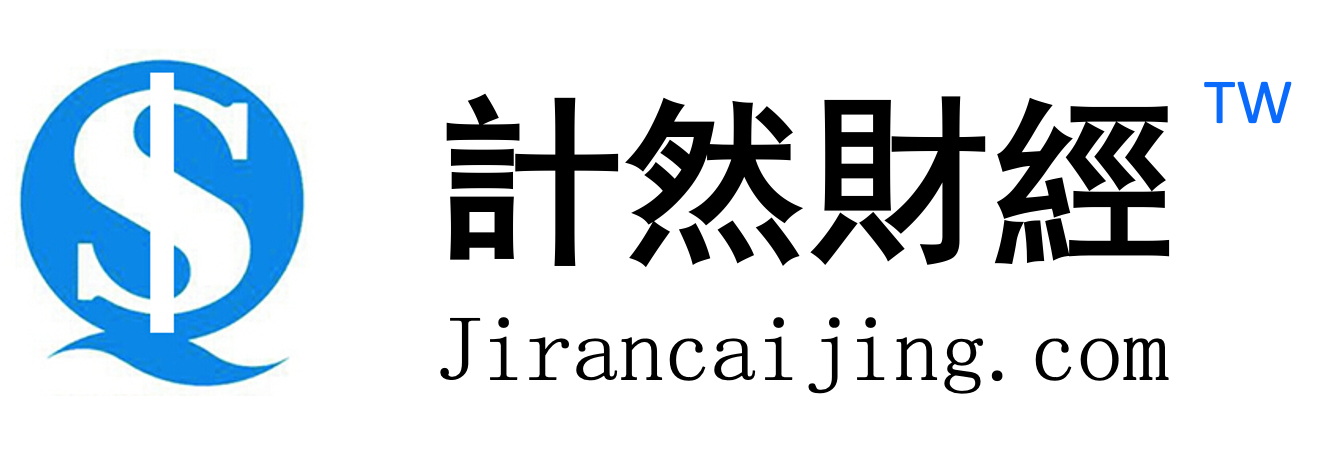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